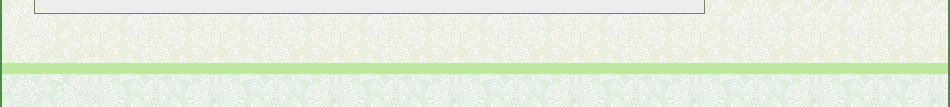长篇小说《枫林传奇》自序
信念的力量
在这个平凡的社会中,很少会有第二个行业,会有这么多的普通、平凡而优秀的人,在他们的平凡的岗位,用他们不平凡的意志,在六十年间,为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创造了如此不平凡的业绩,他们几乎在一种不为人知的状态中——在深深的井底,在无尽的黑暗中,挥洒着汗水,呼吸着粉尘,忍受着牺牲,默默走过了他们英勇无畏、勇于拼搏、充满伤痛却坚忍沉默的平凡的人生。是一得付出而没有索取、牺牲并没有回报的人生过程。这是一个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和两代人以及三代矿山人生活开始启程的艰难的人生之旅。
长篇小说《枫林传奇》的地点是在一个称之为东南省的煤炭工业局的下属煤矿 。煤矿远离城市,都是在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灵的山区。一个在东南省的煤矿行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枫林煤矿为主要背景写成的故事。小说中的枫林煤矿井实际上东南省曾经的最大规模的煤矿和唯一能生产烟煤的两座煤矿的影子。
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枫林矿务局和下属的主力矿井枫林煤矿的故事。故事内容时间从1958年建矿到2018年关井,涉及这六十年间,以乔子坤、贾志雄、肖桐凯、王婉秋等人物为代表,矿山家庭和军人家庭出身的一批矿山子弟的人生故事。
这部小说共分上、下两部,总计七十六章,有近六十万字。以枫林煤矿主背景,表现了数十个人物的命运,基本上是全景全画幅地表现了东南省枫林煤矿六十年历史的全过程。
小说以主人翁乔子坤一家在煤矿的从一九五八年到二0一八年六十年间的矿山生活以及乔子坤个人在煤矿生活和工作——从儿童时代到参加工作和退休的四十年的工作经历为素材。以一个矿工家庭和矿工个人的煤矿生活岁月为线索,表现这段东南省煤矿从兴起到退出的六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是充满无比艰辛的过程。
江厦铁路的建设是一件伟大的史诗性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培育了他们的革命理想和生产技能,所以他们在矿山的工作中也能很快地脱颖而出,而勇于面对更为艰苦的煤炭建设,这个充满艰辛、充满对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生存极限提出了更为艰苦的挑战!他们一生都在从事艰苦的行业,就是煤矿。他们有的在煤矿能一直干到退休,有的则一直生活在煤矿,历经了六十年的岁月磨难,这本身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都是生命的奇迹。
当年作家路遥在写《平凡世界》就专门在陕西的铜川矿区的煤矿体验了三个多月,并与矿工们一同下井,到采煤工作面了解工人们的工作实况。有一个知名作家曾说,要想全面的了解人类社会的人性和人生————那就要到煤矿去。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中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
在上个世纪的1958年到2018年,有一批人数参加过东南省江厦线建设的铁道兵、民工、干部,又转战和参与了东南省煤矿的建设,他们的人数达到万人。其中不乏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退役军人。他们的命运和生活经历和发生了什么,几十年来一直是鲜为人知的。这个长篇故事,就是有关他们和后代的矿山子弟们这六十年间发生的人生的片断的重塑。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在首有关妈妈的老歌,其实我们都记了一辈子。老歌最真切地讲了过去年代孩子们对妈妈的感情和对矿山父母的感情,也讲诉了他们过去的生活。我的父母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其实我经常思念他们。就象当年他们也经常思念我们一样。当年为了参加工作,我和我的二哥都不得不离开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矿区,而到另一个新建立的矿区去招工。虽然我们已经长大,但是毕竟我们也才十七八岁,虽然已经能够独立,但是我们依旧对父母有着很深的眷念。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1963年在参加干部开梯田义务劳动中,我父亲将分到的作工地午餐两个红糖馒头分给我和我弟弟,而他空着肚子开了一天的梯田。
我们这一年当年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煤矿出生的矿山子弟,如今也都陆续退休成为了老人,我们的年龄也将接近或者超过了六十岁。而我们矿山子弟的父辈们,则绝大多数都走进了历史,只有极少数的长寿者,年龄也在85岁至90岁之间了。
2018年是东南省煤矿六十年了,东南省煤矿煤矿六十年的故事应该老一代人绝大部分已经过世了,如果我们对所经历的这段完整的历史不说、不回忆,已经没人能再说、也可能想说,也可都未必有人还能完整的将这段诉说出来——历史应该记住在东南省铁路和东南省煤炭建设的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批为之奋斗不息的人。这一批人绝大多数都
参加过江厦铁路的建设,从江厦铁路的建设后再转到东南省煤矿的建设中来,他们在自己的有限的人生之中,参与和建设了两项伟大的事业,他们这样的人生足于堪称伟大。
六十年,对一个人,尤其煤矿工人来说,因为煤矿工人的身体由于职业的特点,大多数都没有超过七十岁。不少人在六十多岁,甚至在五十多岁就因为矽肺病而失去了生命。因此,六十年对煤矿工人的确就是一生,对一个企业,也可能就是从兴起到终止这样一个自然的周期。而对一个煤矿行业来说,六十年的建设生产和发展的历史,其中包含着无数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衰退;而六十年历史,对一生都从事煤矿建设的无数企业员工来说,却更为凝重和难忘,因为它包含着无数人和无数家庭和成员的命运兴衰与人生的荣辱、包括难于数说的艰辛与血泪。
艾青说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一批煤矿子弟,其实当年也就无路可走,比如上大学,那毕竟只是极少数幸运者的事,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事。我们即然生在煤矿,也应该勇敢地走入煤矿。煤矿的确是个培养锻炼人的好地方,同时也是一个淘汰人的地方,是历练人生的试金石。
六十年的艰苦岁月,煤矿人为什么能持续坚守,是什么支撑了他们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拖家带口从千里百里之外向东南各个矿区汇聚?是什么在他们的家庭、家人受到巨大的困难、无言的付出、甚至是残酷的牺牲,依然矢志不移,坚持以矿为家以煤为业,坚守了六十年之久?煤矿人精神的核心思想和理念究竟是什么?
曾经有一个兵团战士,是当年矿区的音乐教员,她终身未婚。后来她调回泉州后又出了国,并在澳门一个学校当了多年的钢琴老师。六十八岁时,她回到泉州,此时她已经身体不行了,医生告诉她至多能坚持三个月之多的时候,她选择要坚持回到煤矿看看。她的弟弟还专门为她找了一名懂医护的亲属陪她一起来煤矿。在煤矿走走看看了三天之后,她选择在县城的一个很老的酒店住下,并安详的睡眠中磕然去世。这个女兵团战士、一个音乐教员,终于凑完了完了她人生最后一个乐章——回归大地。
可以想象,一个行业、一个矿区和一个社会的角落,有数万人,历经了几十年的奋斗和牺牲,甚至还影响到第二代人、第三代人,这样一个现实生活,竟然在当下的社会和历史中没有任何真实的、文学性的记忆,甚至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对煤矿工人来说,也真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作为一个煤矿企业的政工人员,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一个煤矿采掘工作的经历者、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觉得我个人的想法其实也并不复杂,在那个历史中,我本人也只是一个经历者或者说是参与者,并不是当时的权力者,以及后来退休之前也从来都不是,而只是和广大的普通干部和基层的工人一样,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对那个在艰苦岁月的磨难,人们是不会轻易忘却的。我觉得的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必须将它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
,要让我们的后人,了解什么是煤矿,什么是人类在煤炭生产这个另类的历史中有这么一种无比艰辛的奋斗。在这种为了国家的强盛而付出的整整两代人的艰辛奋斗中,他们创造的精神的价值要比物质的价值重要的多。可以说,与煤矿工人的生活相比,人世间已经没有什么艰难的人生可以同矿工们的人生的艰难相提并论。
我离开煤矿这么多年以来,这些事情总是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有时候真的是将我折磨得十分痛苦。我都一直沉浸在对过去亲身经历的煤矿生活的回味中。退休之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其实并不怕年老死亡等常规的在人的一生中必然会遇到的这些自然规律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将这过去这几十年的煤矿生活的体验写出来,却是一种社会煤矿文化历史的浪费。
煤矿工人中的手艺人有一种特有的编织方法。我从中获得了创作的启发和艺术的灵感,从中领悟出了煤矿文学创作基本手法。在煤矿的采煤工人中,有一种堪称为艺术的手工艺活。这就是矿工们用在采煤工作面放炮之后在从工作面放煤中,或着在地面筛选厂的捡矸过程中,人们从中拾取的一种色彩斑斓的放炮线,有红、黄、蓝、黑等多种色彩。这是一种包着塑料皮的细铜丝线,用作放炮中与雷管相连通电的导线。大多数人是看不上的,但在一些手艺巧的矿工眼中,这全是难得的宝物。他们成年累月的坚持捡这种有用的炮线,完整的炮线不会再有了,它们在爆破中早已经支离破碎。矿工们只能找出爆破之后的残余线条,是一段一段的粘上了煤粉的线条。他们就收集起来,洗净之后依照色彩的不同,分门别类存好,线条足够了,他们就先设计出各种造型,用铁线做成框架,依靠这些残线,在框架上编织成各种巧夺天工的手提篮等用品,这些很实用的手工艺品,令人叹为观止,
这也是矿上女人们的最爱。放炮线也因此获得了新生。
因此,将生活中的漂亮的、生活的、感人的各种事例整合起来,根据小说设计的构架,编织成矿山的故事,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否则随着岁月的流失,这种感人的矿山记忆,将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这种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在全国煤炭 “关井压产”的今天,南方的国有煤矿又面临着一次空前的撤出,东南省的矿工们同样坚守信念,服从安排,自己继续寻找新的生活道路。
那块当年在漳来煤矿山道上的碑刻上有永恒的四个字能解释他们不变的伟大情怀,那就是“建设祖国”!再没有比“建设祖国”这个思想内涵更重要的意识能更深的植入和体现这一代煤矿工人的伟大灵魂和感人的情怀。也没有什么话语能比“建设祖国”更能浓缩他们以自己一生为之奋斗与牺牲所追寻的人生的根本价值。
2018年11月23日
再修改于永安下渡梅园
作者